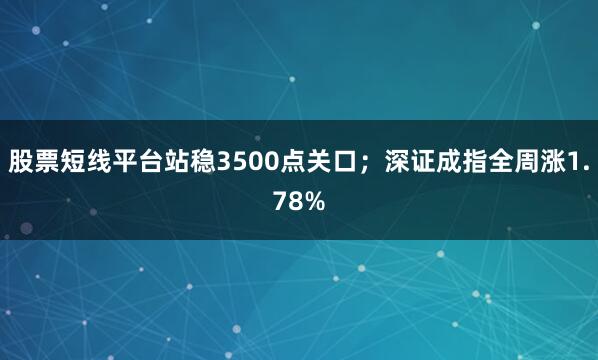过去两年,AI 生成代码的Demo一个比一个炸裂:
一个 prompt,整个应用直接出来;几句自然语言,啪的一下,一套后台系统就生成了。
看上去,软件开发似乎要进入“无限加速”的时代。但现实的魔幻程度只有身处其中的团队有体会:
相应上线的产品数量并没变多,也没看到期待的创新速度,甚至不少团队感觉比以前更累。
谷歌一位工程副总裁曾说过一句很扎心的话:
“如果大家知道 LLM 生成的代码真正进到生产里的比例有多低,一定会非常震惊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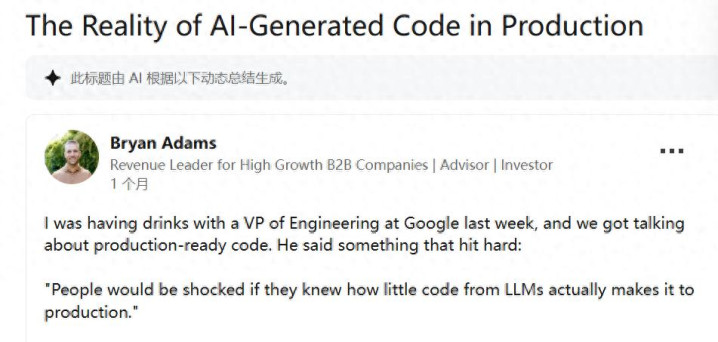
为什么从“100 行代码 1 秒出”到“上线”之间,会有这么深的黑洞?
近日,一位技术背景极丰富的AI初创公司PlayerZero的创始人 Animesh Koratana 给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观察。他指出,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因为大模型还不够好,责任页并不是出在 AI Coding 产品侧。
答案其实很简单,但常被忽略:AI 写代码强,但生产环境不只是写代码。原因主要来自三个根本挑战:
全新项目(greenfield) vs 既有技术栈:AI 在没有约束的原型环境里表现极佳,但在真实生产环境里,它面临各种硬性限制,代码会变得非常脆弱。
“多莉问题”(Dory Problem):AI 无法持久理解,也记不住自己的行为,因此很难有效调试代码。
工具成熟度不一致:代码生成工具进步极快,但部署、维护、代码审查、质量保证、客服等工作流程仍停留在“前 AI 时代”。
一、AI 在“真空环境”里很强,一接入真实系统就露馅
AI 擅长的是“从零开始造一个东西”。在真空环境中,LLM 可以很快起草出一个新的微服务,并且在隔离情况下运行良好。
开发新软件其实是一种“艺术过程”。你从一个想象的行为路径开始:数据如何从初始态流向最终态,如何被转换,如何被控制流处理。这种“从无到有的创造性过程”,AI 完成得非常漂亮。
这正是为什么 AI Coding 的原型效果如此惊艳——它擅长面向未来的、无约束的创造。
但绝大多数生产软件,并不是从零开始造,而是接入一个堆了 10 年、20 年的系统。
只要进入生产,在用户使用这款软件之前,AI 就必须接入各种“真实世界的混乱”:
各种历史遗留代码、服务边界、数据契约、认证逻辑、protobuf schema、CI/CD 流程、可观测性体系、SLO 与性能预算、若干代工程师留下的补丁……
随便一个环节,就能让原本“完美运行”的原型代码瞬间脆到不行。
生产环境下的软件,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“写更多代码”,而在于“写在严格边界内也能正常运行的代码”。
而把这些复杂、细腻的运行参数都准确传达给一个 LLM,本身就是个艰难的任务。
可能因为 LLM 能用自然语言跟我们交流得很好,大家自然就高估了它写高质量软件的能力。但语言是宽容的,代码不是。代码是可执行的、结构化的,它的正确性必须跨文件、跨服务保持精确契约。
毕竟,编译器和运行时可不会对错误留情:小错误就能导致级联故障、安全漏洞或性能崩塌。
AI 还停留在理想国,工程师却活在人间。AI 写的代码不稳定,不是因为它不聪明,而是因为它还不知道真实世界有多么艰辛复杂。
二、“多莉问题”:5 秒前发生的事它就忘了
现在,我们已经知道当前 LLM 在受控环境之外写代码有困难。那还有一条思路,即,为什么不能反过来让 AI 来Debug这些代码?
想法很好,但遗憾的是,真正的 Debug,需要的却不是大模型的“聪明”,而是:
读懂几十年累积下来的系统架构,以及它为什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
弄清楚数据真实的流动方式,而非设计文档中的理想流动方式
理解历史遗留的每一个 workaround
追踪多个代码仓库的交互
从一个缺陷逆推整个系统的状态
换句话说,你需要理解系统的“当下”和“过去”。但绝大多数 LLM 的思维方式更像《海底总动员》里的多莉:上下文极短,没有记忆,无法把前后语境联系在一起。
“我是谁?我刚刚做了什么?算了,从头来吧。”

当你的代码库有 20~40 年的维护历史时,这种记忆模型根本不够用。这里面有涌现的行为、隐含依赖、历史妥协,是技术债务的复利。
没有对整个系统架构的广泛理解,没有对多个代码仓库、历史变更、过去发布情况的掌握,你几乎不可能调试真正复杂的问题。
这也是为什么 AI 可以快速生成一个“看上去能跑”的模块,但当它试图修自己写的 bug 时,立刻跑偏。AI 缺的是“持续理解”,缺的是“系统级记忆”。没有记忆,就没有真正的调试能力。
三、工具成熟度不一致
AI 代码难以在生产站稳脚跟的最后一个原因,是因为支撑整个软件生命周期(SDLC)的工具成熟度并不同步。
这里,历史上也有一个可类比的例子:数码相机。
最初的数码相机只是模拟胶卷相机的外形,只是“把数字技术塞进旧框架”。
但一旦人们明白可以用更广的想象空间,摄像头就无处不在:电脑、手机、门铃、汽车。它现在已经不止用来拍照,还可以用来导航等等。
AI 代码生成工具也经历了类似变化。
第一代产品(例如最初版的 GitHub Copilot)就像“把 AI 塞进 IDE”,本质是超级自动补全。
但近几年,Cursor、Windsurf、Claude Code 等产品彻底改变了工作流:你不再写代码,而是在对话框里表达意图,代码自然发生变化。
可见,现在的代码生成已经进入第二代,重新定义了编码方式。
但这仅仅改变了“写代码”这一段。软件上线不是写完就完了。剩下的流程都没跟上 AI 的速度:
代码生成之外的 SDLC 其他环节——部署、测试、维护、支持——还停留在第一代。
这就造成了很尴尬的效率不升反降的境地:
AI 嗖嗖地加速写代码,人类却在泥沼里给AI修Bug。
如果我们真的想提升工程效率,就必须超越“写代码”这一步,重新想象整个 SDLC 的工作方式。
四、前路在哪里?
今天市场上有很多致力于现代软件运维的工具,更多还是在老流程上贴 AI:
AI 代码审查、AI SRE、AI 文档助手、AI 监控助手……
但这些工具往往是“各管一段”。它们依然在打造各自更好的“数码相机”,缺乏从零重塑整个流程的想象力。
固然,一个更好的 AI 代码审查工具或一个 AI 版本的 SRE 能带来增量效率提升,但真正的突破,来自重新设计整个端到端的软件运维流程,而不是给旧流程“上一层 AI”。
未来能在生产环境真正帮到工程师的 AI 工具,将会具备这些能力:
能逆向解析复杂系统
能系统性枚举所有状态
能帮开发者找出导致异常行为的具体条件
既能“艺术创作”,也能“科学调查”
它们必须整体地看问题,而非割裂处理。
在那之前,相信我们还会继续看到冰火两重天的“奇观”:原型很惊艳、生产环境体验却糟异常糕透、无数令人抓狂的生产事故。
而这种“认知错位”,本质上并不是AI或大模型的责任,而是AI与生产环境之间的“代际差”所决定的。
当然,代际差不会自动消失。它必须靠新的工具、新的架构设计方式、甚至新的工程文化去解决。
启天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配资讨论网几近第二至第十名销量总和
- 下一篇:配资头条官网面料挺括又带着棉的柔软质感